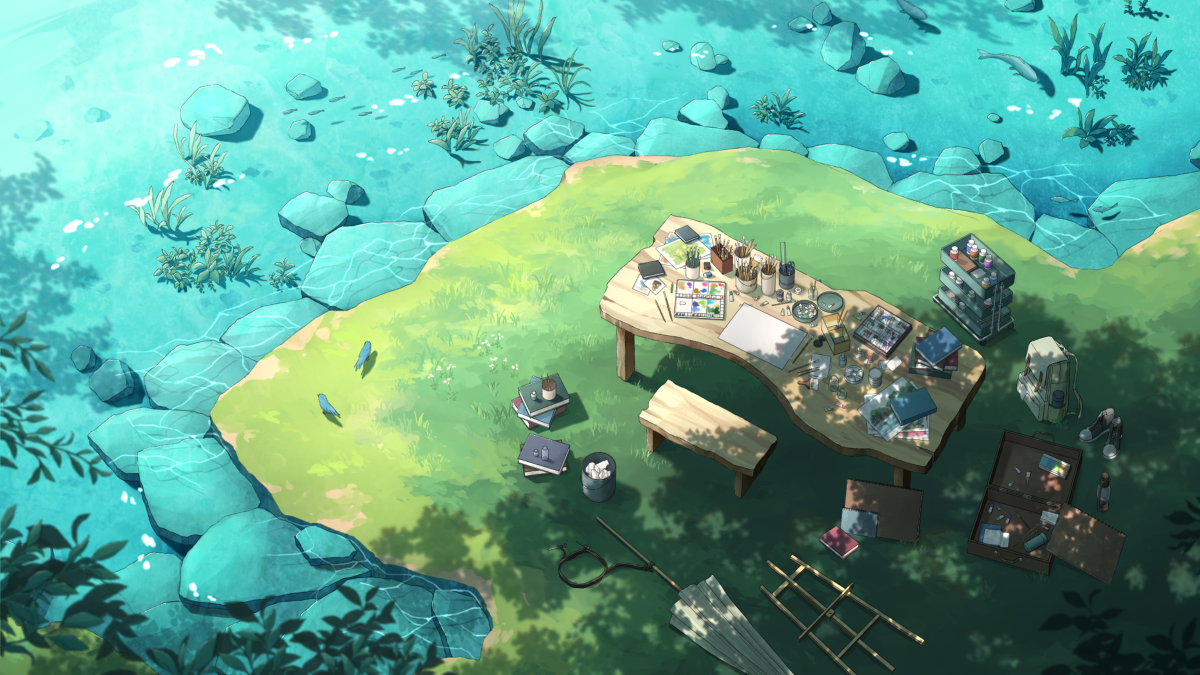不思蜀
元宵节过完,发现应该回去工作了。
但最近在老家待着什么都不想做,也提不起兴趣回省城。
春节这半月一直断断续续的在下雨,屋子的周边有稀泥路,显得有些脏,也就不愿意出门。房子里多数时候只有我一个人,牲口些也在远处的田埂上,屋子里听不到叫声,只有屋后竹林窸窸窣窣的声音和时不时传来的鸟叫。也没让我感到寂寞,城市里很吵,静不下心,而这里能得安宁。
每天早上得早起,天刚亮,起来煮红薯、菜叶、玉米和米糠给牲口吃。我爸在家里养了七只鸡,十二只鸭子和三只鹅,一头猪,数量并不多,但手脚却不少。弄完之后我也偷它们半个红薯吃,就当早餐了,然后回楼上继续睡觉。
这几天很冷,若是早起,更是冷得浸人,坐在灶前烧起了火开始煮东西,火升起来了便感到很惬意的回暖。
搬家
这个年过得很安静,镇里不许放烟花爆竹是一个原因,使得扫墓的人少了很多,大年晚上也只看到三两家没什么底气的烟花。往年初一弥漫一整天的稠雾浓云,今年十一点多便渐渐散了。
却也没太阳。
另一个原因是今年从镇上搬到乡下来住了,虽说镇上的屋子也还在,而且老家距离镇上也只有五六分钟车程,但这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决定,这个决定打破了许多往日里的细节设定。我独自拆掉了镇上房间里的电脑,打包了多年的衣服、布偶、玩具和以前的书本,全都搬了回去。然后假装顺口一提的和三五个朋友说起“今年我回老家了所以除夕不能一起跨年,我们初一再见。”
但是初一下起了雨,出不了门。
和以往的很多次一样,这可能也是一种我潜意识里的预感,说不清道理,只想着应该这样做。往年一起吃零食跨年的日常我想怎么挽留也留不住,总有一天我会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独自跨年的,而且似乎就该在今年。这种感觉像是旅人走过了桥头,回望来时的闹市,那边酒旗灯花,戏鼓轻踏,暂歇一口气,耳边的人声散去之后,还得继续往前走。
小佩和九曲在一起了,他俩去年秋天才和我说。
我认识他们各自的时间比他们认识彼此的时间要长很多,他俩经常在一起,所以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稍微有点惊讶,却也并不意外,以后写一篇他们的事情。
他们在一起之后和他们处在一个空间里我会觉得不太自在,分别和他们各自相处时倒是觉得没什么变化,但和他们俩一起看电影我总觉得周边弥漫着什么东西。
当然,他们在一起并不是我决定搬回老家的契机,只能算是一个磁场,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潜意识里的决定。
街上这个屋子是我爸弄的一个工作间,只有十多米见方,楼下是木工门市,楼上算是我的专属房间,虽说不大,但卧室、洗手间、厨房和餐厅都有,三四个朋友也还会得过来。从我初中起这个屋里便没有家长,而且这里有电脑和电视,在过去很多个跨年夜里能和几个朋友轻松惬意的这里吃零食,喝小酒,看春晚,一起跨年,凌晨的时候再一起去欢欢家找他和他爸妈一起去烧子时香。
初中时候这里算是大家的秘密基地,因为那时候我一个人住,和他们家里相比这里会更自在。
九曲家开的超市,我在家的时候他会带些零食饮料过来一起吃,出发前给我发消息,问有几个人在。我们偶尔也会去买一些,欢欢时不时也会带些饮料或者街边小吃过来,还喜欢顺路租两三张光盘。小佩则空手就过来了,只在门口问一句我爸:“小郁在家吗?”,或是不见人在门市上,自己走楼梯就上来了。
城市并不属于他们,城市甚至不属于任何人,美好的回忆、痛苦的回忆,这些都属于人自己的,而不属于城市,城市并不会为一条街道的消失而哭泣,会为之流泪的,只有人而已。
他们想守住的,想留住的,是自己记忆里的城市,是让自己玩闹、成长,让自己跌倒、热血的那个城市,他们想守住的,是自己的痕迹。——山行、叶子 · 评《恶童》
关于镇子里房子的事情以后想起了再细说,乡下这间房子,我十年有余年没回来住了,虽说房子里一直有住人,而且每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也会回来吃饭,但多年以来都去镇上的房间里过夜,不曾留下睡过觉。
这次回来住让大家觉得挺新奇。
大年初二,兰湘路过门口,对我感叹说:“有没有感觉到今年空气好些,都没觉得不舒服。”
兰湘对空气很敏感,刻意避免靠近马路,在疫情之前也是戴着口罩才能进城。平日里村上来往车辆很少,倒也没事。一过年大家都把车回来了,村里的单行道变得很挤。车太多了她也会经常咳嗽、流鼻血之类,吃了片方,看了医生,却也没什么效果。不出门倒好一些,但作为生活在这里的人,过年一直在家里不出去见人也不行。
我问她要去哪里,请她进屋坐一会儿。
她说先不了,晚些再来,王家的老爷子昨晚去世了,她带了点钱去看看情况,问什么时候成福,好去帮忙。
见我靠在场门上没接话,她慢慢的指着西方说:“是观音桥头右边的那个王家,青瓦楼房,坝子门口有个大石磨那儿。前年国庆我们路过那家,当时你还说去偷个柚子的那儿。”,我连忙点头说:“喔,原来是他们家,我想起来了。”
光环
她总这样和我说镇子里的人,桥头路口,山坡下池塘边,什么样的房子,或是从哪里的第几个坡第几个弯的左边右边。
我不认识镇上的人,甚至不眼熟,连老家房子周边的两户人家都不知道名字,高中之后我走在镇子上也都戴着耳机低着头,不认人。我不理他们,他们也不理我,爸常说这样不礼貌,但那时的我就是把仇恨都平均到了镇子的每一个人身上,没兴趣对他们表现礼貌。
兰湘的高中在自贡,而我在泸州,假期里能见面,因为距离不算远,也去彼此的学校碰面过几次。我高二的时候渐渐意识到这个细节,兰湘知道我不喜欢这里的人,那年在我第一次问她“你说的这个明天要结婚的光进哥哥住在哪里?”之后,她楞里一下,之后便渐渐的不和我说起这里某个人的名字或身份,有一种“算啦,你也不用去记他们”的意味。
我也吃她这一套,多数时候我对不上人,想到了之后就恍然大悟的说“哦是他们家”,或是本来就知道,便说“嗯嗯,我知道他们,他们怎么了”。
大学去南京念书,学费挺贵,我便想着要去申请贫困补助,打电话去南京那边问了流程,说做出表格要村长村支书以及县教育处写推荐书签字。想到县城教育处的推荐书倒是小问题,我成绩并不差,提前打电话问清楚,然后坐车去一趟,找对应的人跟着流程办理下来就好。但村里的事情我却有些犯难,便开口问兰湘我们村的村支书是谁,问她认识么?
她那时候在站在窗台边削橙子,拿着水果刀在屋里渡了两步,转身对我笑着说:“他一般在老街茶馆里,住在场口卖鸡鸭那一家的对面楼上,你应该没见过他。把资料给我,我去让他帮忙写吧,就说你已经去外地的学校了不能亲自回来。”
那是第一次需要找镇子里的人帮忙,她稍加思索便替我挡下来了,至今还记得当时她身后闪亮的光环,而后的许多日子里她在我的记忆里都是那个形象。
下午她便骑自行车载着一件牛奶去找镇子里找村支书了,我说和她一起去,她说这样就露馅了你不能去。明明比我小半岁,那一刻却感觉她更像一个姐姐。
回乡
兰湘家离我家算不上近,现在走路也得二十多分钟,往些年的路不好走,感觉更远,却意外的和她关系很好。那是很小时候的事了,都还没到念书的年纪。到二年级结束,一场变故,我跟着爸去了浙江,不知这一去便过了好些年。
回来的那天我深夜才到镇上,第二天一大早她便来我家找我,站在门口张望,看到我,才走进院子,只说:“我听闽叔叔说你们回来了。”
那时候她说得轻描淡写,仿佛这些年我只是出门度过了一个暑假而已,而我今天回来了,她也还在。
那年寒假有些别扭,镇子里许多人和事需要我去适应,但也只是一个小孩子,跟着玩儿了半个月也都融入了。我爸忙前忙后,说以后不去外地打工了,要把房子弄得漂亮些。翻新院子,疏通阳沟,重修灶头,新打水井,还让我去渡口买鱼,邀请了几个他的朋友来家里喝酒。第二年开学,我回到了镇里的学校,和兰湘一个班,她还是和我走得很近,仿佛和之前一样。
那时候她总问我在浙江做些什么,有什么有趣的事情,我说在城乡结合部住着小平房,宁波很大,但是房子很小,三个人挤在一起,也没有院子,没有阳台,种不了橙子树,也养不了花,告诉她浙江的话我听不懂,和他们要说普通话等等。
之后的那些年几乎和她去了镇子周遭所有的地方,走过所有的田坎和山路,远一些的地方走了两三个小时去玩儿,傍晚天黑了借路旁人家的电话打过去让她哥来接我们。
那些日子我一直铭记于心,并照亮了许多往后的灰暗岁月,这可能也是她能很具体的和我描述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的原因。
人间
想了一会儿,问她说:“你是打算去帮忙么?”
“嗯,去慰问一下。安葬这些事情,操办起来很繁琐的,去看看有没有能帮忙的地方。”她眺望着那边,又缓缓的说:“爸一早就过去了,村里的习惯嘛,去帮忙切菜洗碗,我也没别的事情。”
却也没帮上忙,过去没多久便回来了。
到我家门前特地停了一下,将手臂上的白布摘下来卷了卷,揣进衣兜里,然后推门进院子,家里养的狗听到她走进门的声音便很熟络的迎了上去。